第一次感觉水的沉重与粘稠。缓慢地在眼前滑过,扭曲了的空间,加上昏暗天色下反反复复光的折射,似乎被水银附身了,眼前银色一片。车子挡风镜遭遇前车之“溅”,小生被浇了一头灰水,四肢僵硬,好不容易踹了煞车板几脚,车子渐渐凝滞在那一刻,左手慌乱地拧开扫水器。水扫漫不经心地挥手像是受不了小生的急躁似的,兴致索然地操作,许久没能让视线复原,煞车器快踩到底了。
雨势暴戾,行驶的车子更暴力,仿佛扫帚星甩出的一道水花连成的飘移线,一点一滴汇集在小生车镜上。脑子一阵嘀咕“完蛋了,快撞车了”,直到没有预期的声响,没有预期的模糊,直到挡风镜回返清澈,视野才开始,安然无恙——第一天代班的路上。
老爸老妈赴上海参与二姐的毕业典礼,家中老弟还没到令人放心的年纪,店铺里阿姨一个人又忙不过来,小生于是充当几天的临工替阿姨看店,挤出一点时间来让阿姨喘口气上个厕所什么的,顺便打包午餐,扫扫地,帮着收店。星期六还到学校去假冒家长,帮老弟骗了一张成绩单。那班级任在名单上写了个“兄”,然后旨在与老弟攀谈,正眼也不看小生一下,想让小生从侧面了解自己弟弟在学校的状况。毫无意义地,三分钟内一切结束。
看店的时候小生怕生起来,对走到面前的顾客支支艾艾半天答不出话来,然后大声求救“阿姨,阿姨”,顾店门的小孩子一样,只懂得凑热闹,正经活儿一点也不会干。把顾客交给阿姨,拿了本书匆匆到没人的角落,埋头不敢和谁眼神接触。听说小生是妈妈的孩子,顾客大多愿意多问几句,其中一位auntie问小生是不是马来西亚人,“how come you don't speak Malay?”小生一窘,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中原委太冗长,听得任谁也要打哈欠,一手捂口一手微甩,不耐烦地阻止小生讲古下去,但就是有人爱讲,爱加油添醋地讲,天花乱坠地讲。小生偏偏愿意受一点委屈。
星期六下午,意外地邂逅了老婆一家人。Larkin巴刹这老气的地方大概很难遇到朋友,除非在楼下湿巴刹买菜,除非要做一套Baju Kebaya、Kurung……老婆也很讶异,还怪起小生怎么从来没有提到自己老妈是裁缝的事。中学时代的小生嫌少公布自己的家底,以前老爸批发香蕉,小生不好意思跟朋友说,总觉得朋友会笑话,所以老是对外宣告:老爸是卖水果的,紧接着主要夸耀老爸的副业——一个“搞华乐的”。同理证得,小生也不会告诉友人说,老妈是“帮马来人(这里被人听起来好像带有贬义)做衣服的”,而是时装裁缝,不过没有副业。
马来人(惯用法。本想用“马来同胞”,又觉得不小心就沾染了政客的恶心,于是还是用“马来人”的好,没有贬义)逢年过节都要制作一套传统服装应景。这一行的模式是让顾客自己带来预买的布料,然后量身、订做:什么样的领,什么样的袖,车花抑或车边……kebaya是上下衣分开的,kurung是连身的……马来服装很贴身,像旗袍、越南装,很能凸显女性的身段,只是裙脚不开叉。Hari Raya将近,络绎不绝的顾客说明了马来朋友都很乐意用传统包裹/打扮自己,或是另一种怀旧美学新的再现。小生思索了一番,觉得没有必要反问(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不流行穿自己民族传统服装的老问题。如果要追溯,大概要回到五四运动时期吧,一切都不那么单纯,于是又懒得去解释,心知肚明就好。
顾客总喜欢在午餐时间或临关店的当儿上门,阿姨只好撇下热哄哄的食物,招呼客人,老妈上班的时候大概也是如此吧,想的当儿饭菜也凉了。星期二小生吃剩的午餐盒子里躲了一只蟑螂,招呼客人后阿姨还让小生再多吃一点。拾起筷子,蟑螂兄熄火的坦克般一动不动,长长的触须迎风摇曳,相当恶心,小生不禁抓狂起来。阿姨津津有味地吃着,冷眼说,换双筷子,别去管它。小生还是忍不住一定要让蟑螂兄撤离容器,随手一份报纸压在上面,翻转后,伺机想解决掉它。没想到坦克瞬间启动,一个黑影攒动,霎那逃离埋伏圈。恰恰阿姨吃饱了,从小生手上取回容器,兀自到厕所去清洗。
来了顾客,问nyonya到哪去了——小生只道这是马来人对裁缝的俗称,回家翻了翻《Kamus Umum》,才发现原来nyonya用作对已婚妇女的称谓,其中并无关于“娘惹”的注明。或许是字典不够全面的关系。“娘惹”一词,对小生而言反倒不如nyonya亲切。nyonya的读音,仿佛nyonya粽一样,符号底下蕴含了香、咸、辣的滋味——回过头,小生支支吾吾尴尬地微笑,旋即把顾客交到阿姨手里。
代班后到Kayu家一趟,预备要录一份伴奏带。出外借了一台keyboard,却没有USB电线,几经波折,最后还是以最原始的方法,直接用麦克风收音。很迟才回家。自己随便炒了一碟冷饭,衬着冷饮吃了。回家的几天,只为老弟准备了一顿晚餐。冰箱里快坏掉的都拿了出来,煮了一锅杂菜汤,炒了一个油墨,开了排骨罐头,最后加上一片香煎鱼排,分量恰到好处,一点也没剩下来。老弟给足了面子,不枉这几天充当他的免费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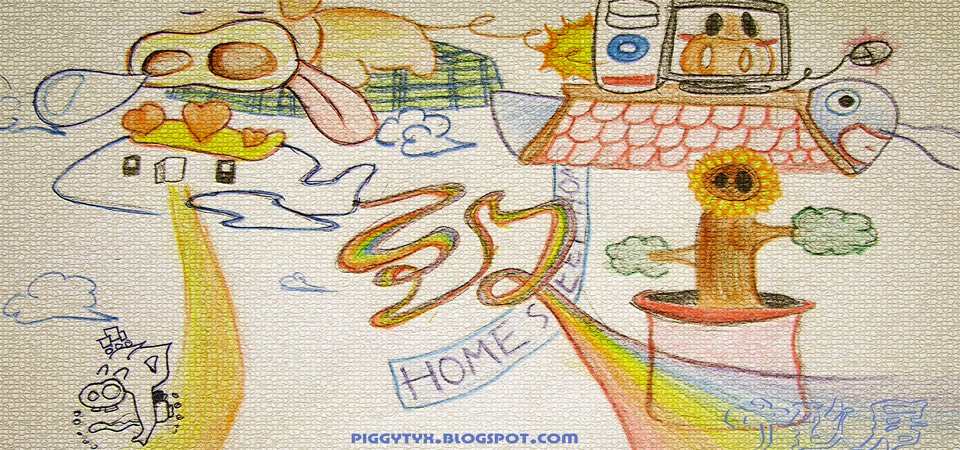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