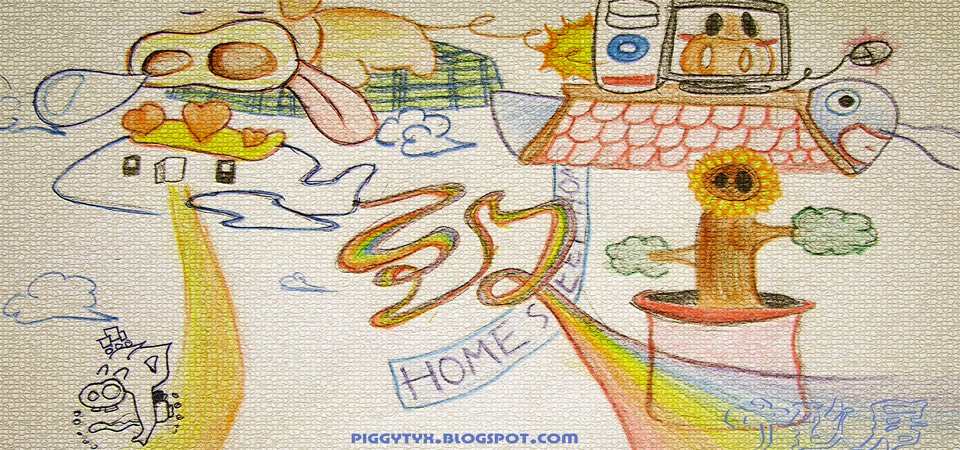老妈说,我的照片在电视新闻里闪现,下面注名“牛油小生”。那张白白净净的脸,老妈很开心。
知道获奖的消息,是第二天的早晨,在前往吉隆坡的途中,二姐发来的简讯。清早6点起身,走在马六甲的街头,天还没破晓,车辆稀疏,偶尔有灯光掠过。等不到德士的我,最后反倒上了公共巴士,辗转来到车站,胡乱买了车票就出发吉隆坡。巴士到吉隆坡转站,要去槟城,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在半山芭下车,很快就抵达花踪研讨会的会场,我像个贪婪的债主,见到工作人员便催着要领奖,快没把他们吓坏。
我原是多么害怕出席了典礼却没有得奖的那种落寞。当我站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的舞台上,台下几百双耳朵正浸淫在我们美妙的和声之中,我几乎忘记了花踪这件事。这个美妙的星期六,我们从新山启程马六甲,漫不经心地走了两遍鸡场街,吃那出名的煎蕊。大哥说,还不如那经常出现在他家门外的印度小贩,脚踏车还有吆喝声,那才够味。或许如此才解不了暑气,大伙儿在彩排时声音暗沉,热汗直流,疲乏得很。青瑞拇指和食指展开闭合,凭空画了个圈,宣告排演结束,众人意兴阑珊地踱步,没入主办单位为我们准备的简陋的冷气休息室。
有冷气,那就足够了。
可能是精神恢复了的关系,正式演出时出奇的好,一段段旋律从嘴里流淌而出,偶尔因为很累就快力竭声嘶了,却始终挺着腰杆子将歌曲完成。我喜欢和声饱满的曲子,我喜欢悬置后纾解的终止式,我喜欢Irish Blessing第二部男声作为伴唱时柔靡的张力,用很轻的高音去拉扯和旋的色彩,仿佛弹拨天上的虹彩,我喜欢成为和声的一部分。
但写作是孤独的。研讨会上播放了王文兴老师的纪录短片,他的文字创作历程触目惊心。那种字字玑珠的追寻,完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尤其懒人如我。焦桐也说了,不大量阅读如何写作——带着羞愧,我怀疑地凝视奖杯上那非人的名目。
〈流水丹青〉写于2010年杪,赶在花踪截止之前。缘因观看了一场羽毛球比赛的网络视频,想学古人用文字记录我们生活所及的种种,却越发与记忆纠结一处。我虽满意于这篇散文的结构却始终不认为它能得奖。获得评审青睐是意想不到的,当我接获二姐的简讯,竟一点兴奋感也没有,只想着要睡觉。
我一从吉隆坡回到家,老妈便很心急地要一睹散文的内容,读到一半她说,明天要请薛老师吃饭。为此,我印了文章,修修边幅,简单地装订,贴上封面制成小册子。散文写的是童年时代学习书法的情怀,薛老师是我的书法老师,我一直都唤她作薛老师。小学六年的每个星期六中午,我都到老师家里学习书法,当时看其他小孩嬉闹在一起,我很羡慕,却不知为什么总是害羞不敢过去玩,几年下来却没有认识几个朋友,所以认真写字时最亲的就是老师,她会牵起我的手教我写字,把我的作品贴堂。我稚气的荣耀感全来自书法,校内校外书法比赛,我都参加,偶尔获奖,那奖杯竟夸张的高,俨如中古骑士的刺枪,奖盘比家里盛咖喱的瓷盘还要大,却什么也装不了。多么虚荣的童年啊。于是书写时,不经意便渲染过度,墨汁浸湿了记忆的宣纸。
在合唱团呆了将近十年,《花踪之歌》是陈徽崇老师四大名曲之外最令人喜爱的歌曲了。高歌了这许多年,从来就没有想过,歌声会化作一座锡雕,立在我的掌心。
后记:
我向来无法在长途交通工具上睡着,那天却意外睡得很沉。
感言或如梦呓:我要感谢薛老师,我要感谢这个时代为我们挥洒汗水演绎的李宗伟和林丹,也要感谢所有愿意阅读我的文字的家人朋友。其实我还给花踪投了一篇小说,没有入围,相信水准太低初审就给投篓了。一直以来总觉得小说家的衔头比较张扬,但其实还好,最重要还是文字要有人欣赏。而得奖的意味,差不多就是有多一些人欣赏,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