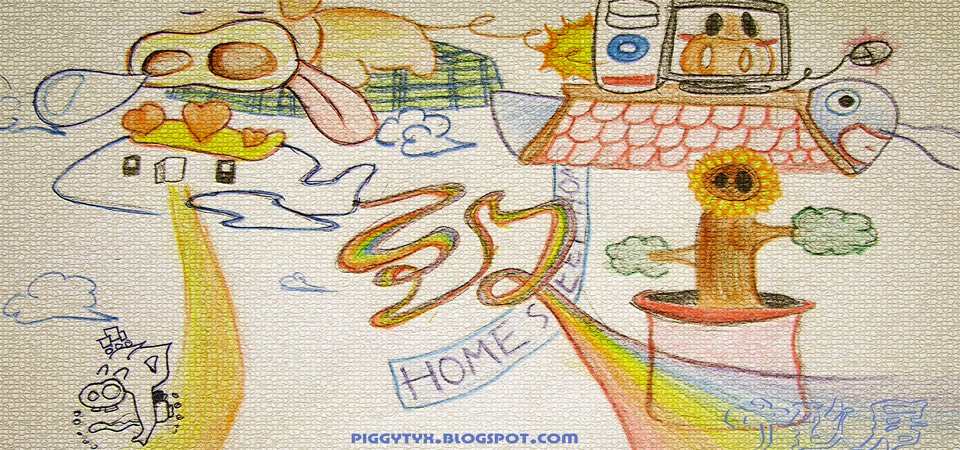只有在夕阳西斜的时刻,“十二门徒”(Twelve Apostles)才能焕发其诱人的神秘光彩。我们驱车来到那里已是临近傍晚时分,太阳正朝海里坠去,我们在晚霞被烧红前攀上观景台,那天的气候颇佳,虽是5月冬日却连薄雾也没有,视野开阔。
十二门徒是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上最著名的景观,原是一系列耸立在海岸线上悬崖峭壁之外的巨型风化岩层,其形各异,高矮胖瘦,最初当地人怪可爱传神地以母猪带小猪的比喻形容这些巨岩,但似乎后来因为旅游业的关系而被浪漫地附会成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披上神话的想望。亲自来到现场,算来算去并不符合一十二门徒的数字,看板上说,一些早已风化殆尽,或说有九尊石板石柱,其中一根已在2005年倒塌。或许数十载后现存的岩层也将不复今日之所见,这些高达四五十米的岩石经不起巨浪的冲击,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这也便是十二门徒吸引人之处,因无法永恒而更显珍贵。故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万物唯变,这正也是旅行的意义,每一趟旅程都是决然不同的体验,转瞬即逝。
大洋路位于澳洲大陆最南端,邻接巴斯海峡(Bass Strait)和南极海,一路尽是壮阔海景,车子行进中,一边是波浪堆起千堆雪,另一边则是嶙峋山色,交错而过教人神怡。从墨尔本市以西的吉朗(Geelong)开始,往西延伸241公里,这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凿的山路,蜿蜒崎岖,只容得下一来一往的车辆,一旦遇上意外或是修路工程,车龙大可等上几个小时,况且沿途只有Lorne、Apollo Bay、Port Campbell等几个小镇,自驾旅游务必确保油缸饱足,一旦中途油缸羞涩,到时没有多少方便的油站可供选择。肚子饿了,这些小镇上虽也有为旅人而设的餐馆,但业者往往在夜幕降临前便收拾生意,加上大洋路颠簸难行,路上随时可能跳出袋鼠、沙袋鼠等小动物,路况难测,因此我们自墨尔本市租车以来,便在车上准备一些面包饼干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巧克力,在冬夜里确实有让人精力倍加的奇效。
从大洋路东端出发,会经过两座灯塔,第一座是Split Point Lighthouse,第二座则矗立在大洋路最南端的奥特韦海岬(Cape Otway)上,可购票登塔参观。我们旅费不足,不敢多加消费,在灯塔入口处稍作停留便离开。离开时想说,何不绕道远处欣赏灯塔?仨人便抓起地图,点击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显示屏开始搜索,最终凭感觉乱走一通,总之是往海的方向走吧,于是撞着胆驾入十分僻静的黄土路,行着,突然发现前面有车子停驻,乘客下车盯着树上看,原来是野生的无尾熊。黄土路四周尽是尤加利树,四五只灰褐色的无尾熊几乎与树干融成一体,就在枝桠交织中隐现。野生无尾熊慵懒依旧,攀爬速度缓而滞,找到定点就缩成一团,眼珠子不肯张开多一秒。在旷野中遇上动物界的明星十分荣幸,比起购票进入动物园触摸驯养的家伙来得真实。
下了车才发现满地都是牛屎,湿冷空气却意外的好闻,呼吸起来畅快无比。偶尔也还有沙袋鼠、兔子这些矫捷的生灵从一边窜到另一边的矮树丛里,恬逸而充满悸动,如果跟着动物们再往深处走便是奥特韦国家公园了。
开车继续往西,终于在日落时分拜谒十二门徒,临走时太阳虽已落下但看看天色尚残有幽冥的靛蓝,我们猛踩油门,全不顾时速80公里的限制,来到Port Campbell镇外的“伦敦断桥”(London Arch)。有朋友抱怨说,到大洋路无外乎就是看石头、石头还有石头,伦敦断桥说白了不也就是一个底下被海水凿穿大洞的岩石景观罢了,看起来似桥而已,但换个方式思索,这可是以时光慢慢雕琢的艺术,手法可能粗糙但却总是鬼斧神工让人拜服于那些造型的神采。许多年前,岩层的桥面是连接着陆地的,1990年的一天,桥的中段突然崩陷,两名游客被困在四面悬崖的断桥上,最后被直升机救走,我一边阅读这些资料一边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突兀地配上入夜的海潮声,一波一波,实在不很搭调,却有趣得很。
最后我们摸着黑回返旅馆,才发现大洋路上不设路灯,只有拐角处有反光片,旅伴一时兴起,突然放缓车子,把车灯熄灭,世界顿时陷入无止尽的漆黑。旅伴大概也吓了一跳,马上拧开灯,又惊又兴奋地说:“真的很黑。”
这一霎那的黑,大概就是远离尘嚣最传神的凭证吧。
载2012年3月19日《联合早报·现在·旅游》
十二门徒是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上最著名的景观,原是一系列耸立在海岸线上悬崖峭壁之外的巨型风化岩层,其形各异,高矮胖瘦,最初当地人怪可爱传神地以母猪带小猪的比喻形容这些巨岩,但似乎后来因为旅游业的关系而被浪漫地附会成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披上神话的想望。亲自来到现场,算来算去并不符合一十二门徒的数字,看板上说,一些早已风化殆尽,或说有九尊石板石柱,其中一根已在2005年倒塌。或许数十载后现存的岩层也将不复今日之所见,这些高达四五十米的岩石经不起巨浪的冲击,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这也便是十二门徒吸引人之处,因无法永恒而更显珍贵。故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万物唯变,这正也是旅行的意义,每一趟旅程都是决然不同的体验,转瞬即逝。
大洋路位于澳洲大陆最南端,邻接巴斯海峡(Bass Strait)和南极海,一路尽是壮阔海景,车子行进中,一边是波浪堆起千堆雪,另一边则是嶙峋山色,交错而过教人神怡。从墨尔本市以西的吉朗(Geelong)开始,往西延伸241公里,这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凿的山路,蜿蜒崎岖,只容得下一来一往的车辆,一旦遇上意外或是修路工程,车龙大可等上几个小时,况且沿途只有Lorne、Apollo Bay、Port Campbell等几个小镇,自驾旅游务必确保油缸饱足,一旦中途油缸羞涩,到时没有多少方便的油站可供选择。肚子饿了,这些小镇上虽也有为旅人而设的餐馆,但业者往往在夜幕降临前便收拾生意,加上大洋路颠簸难行,路上随时可能跳出袋鼠、沙袋鼠等小动物,路况难测,因此我们自墨尔本市租车以来,便在车上准备一些面包饼干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巧克力,在冬夜里确实有让人精力倍加的奇效。
从大洋路东端出发,会经过两座灯塔,第一座是Split Point Lighthouse,第二座则矗立在大洋路最南端的奥特韦海岬(Cape Otway)上,可购票登塔参观。我们旅费不足,不敢多加消费,在灯塔入口处稍作停留便离开。离开时想说,何不绕道远处欣赏灯塔?仨人便抓起地图,点击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显示屏开始搜索,最终凭感觉乱走一通,总之是往海的方向走吧,于是撞着胆驾入十分僻静的黄土路,行着,突然发现前面有车子停驻,乘客下车盯着树上看,原来是野生的无尾熊。黄土路四周尽是尤加利树,四五只灰褐色的无尾熊几乎与树干融成一体,就在枝桠交织中隐现。野生无尾熊慵懒依旧,攀爬速度缓而滞,找到定点就缩成一团,眼珠子不肯张开多一秒。在旷野中遇上动物界的明星十分荣幸,比起购票进入动物园触摸驯养的家伙来得真实。
下了车才发现满地都是牛屎,湿冷空气却意外的好闻,呼吸起来畅快无比。偶尔也还有沙袋鼠、兔子这些矫捷的生灵从一边窜到另一边的矮树丛里,恬逸而充满悸动,如果跟着动物们再往深处走便是奥特韦国家公园了。
开车继续往西,终于在日落时分拜谒十二门徒,临走时太阳虽已落下但看看天色尚残有幽冥的靛蓝,我们猛踩油门,全不顾时速80公里的限制,来到Port Campbell镇外的“伦敦断桥”(London Arch)。有朋友抱怨说,到大洋路无外乎就是看石头、石头还有石头,伦敦断桥说白了不也就是一个底下被海水凿穿大洞的岩石景观罢了,看起来似桥而已,但换个方式思索,这可是以时光慢慢雕琢的艺术,手法可能粗糙但却总是鬼斧神工让人拜服于那些造型的神采。许多年前,岩层的桥面是连接着陆地的,1990年的一天,桥的中段突然崩陷,两名游客被困在四面悬崖的断桥上,最后被直升机救走,我一边阅读这些资料一边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突兀地配上入夜的海潮声,一波一波,实在不很搭调,却有趣得很。
最后我们摸着黑回返旅馆,才发现大洋路上不设路灯,只有拐角处有反光片,旅伴一时兴起,突然放缓车子,把车灯熄灭,世界顿时陷入无止尽的漆黑。旅伴大概也吓了一跳,马上拧开灯,又惊又兴奋地说:“真的很黑。”
这一霎那的黑,大概就是远离尘嚣最传神的凭证吧。
载2012年3月19日《联合早报·现在·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