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要走了,我跑下電扶梯,在遠離車站的轉角處攔截。這就是新山,無論到何處,招招手,司機看見了就會把門打開。巴士迎面而來,門甫張開,車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我與車逆向,蹬了上去,撞在門沿上,好在握緊了扶手,一陣搖晃,掙扎踏著梯階上來,恍惚間掏出二令吉七十仙,換取一張打印模糊的車票,逕直走到最後一個座位一屁股坐下。路程顛簸,書裡的文字狂歡亂跳,不讓我閱讀。這就是新山,平靜又那麼張狂,鑲嵌著小小的險峻如寶石如鑽。願意這樣犯險登車,大抵是因為深知錯過一輛巴士意味著什麼,我們總急不及待。如今也只剩下這趟二二五號,行經家門外那條大馬路,回教堂外那小小的巴士車站,每次都鮮少人下車,司機便也蜻蜓點水的,沒完全靜止我就得跳車,一個踉蹌,卻很有那麼颯颯的電影感。
和同事聊天,講起新山的治安,「沒有被搶過就算不得新山人!」——或許被我們新山人講得過於誇張了,但其實生活照常,日子照過,依舊十分恬靜安逸。最近幾場大雨讓家門外那條小河幾次氾濫,來往車子陷在黃泥水中不可自拔,大家相互埋怨幾句,也不十分積極上訴市政府,大多是怨天不尤人,發發洩,不幾天就繼續穿行,行經時還不忘告訴身邊的人,那天才被水給淹了。我告訴同事,某次在書展裡看書,渾不覺書包被人拉開,想起要打電話才發現遭了扒手,頓有種完成新山人身份認同的懊惱與自豪,總可以到處吹噓了,以一個過來人的經歷,堂而皇之,說得唾沫星子都會閃光。那天我沒買書,一如竊賊偷走幾頁黃金屋,卻是黃雀在後。我始終慶幸小偷沒把書包裡的錢包一併探囊取走,算是給自己的一點點慈悲。晚上恰好與友人共餐,才撥電給姐姐要她幫我割掉電話線,一口若無其事地應對姐姐的奚落與責備——為什麼把手機放在背包裡?月底結帳一張兩百多塊錢的單子,全是當天撥到莫名國度的號碼,想想,或許是打回家鄉報保平安的吧,誰能不在那麼一個時刻想起家呢?
高中時班上諸多語文口試要學生分組參與,馬來文課裡老師最鍾愛的就是戲劇演出,要一句句國語台詞的那種戲。我們幾個同學排了一場短劇,對白不多,全是哭爹喊娘的情景。劇情用音樂串聯,有馬斯涅的《沉思》,這首已被戲謔萬千的悲慘小提琴名著,聽著聽著成了粵語殘片,還有《上海灘》氣勢磅礡的前奏,哪怕再加上一曲《小刀會》,課堂內笑聲此起彼落,考試分數完全不要緊了。那時候同學間最喜歡比拚搞笑的本領,博大家印象深刻,可如今想起,倒是十分意外當時竟然選擇為一名攫奪匪銘寫身世,浪漫地為他書寫妻離子散走投無路的境遇,以致走上街頭,風馳電掣地掠攫行人,無情地搶走手機、提袋,乃至性命,荒謬的輪迴。
老爸一次在門外講電話時,一輛電單車駛來,跳下一個男人,罩著安全帽,像假面超人,忽地就是巴冷刀揮落,冰涼的刀鋒抹在老爸額上,鮮血沿著眉間汩汩泉湧,彷彿當年鬧劇中的攫奪匪走入現實,以假面超人的模樣,奪走那台手機揚塵而去,太陽已經落山,灰茫茫,情節如戲。我當時剛打完工回家,口裡嚼著飯菜,聽見老媽的驚喊,一看,老爸捂著臉血淋淋地走了進來,特虛妄的畫面。
生活就是那麼荒唐可愛,診所醫生一邊裹紗布一邊說,快去醫院,我們就匆匆飛車前往那新張不久的蘇丹伊斯邁政府醫院。空調吹得很猛,嶄新的儀器讓人聯想起江口洋介和松島菜菜子的救命病棟,理想與現實膠著的虛榮與使命感。急診部裡護士們坐著放閒,一見我們進來,像一群貓鼬,伸直腰背從座椅上伶俐地彈起,直盯盯打量我們一家不速之客。高聳的天花板迴旋當時氣氛的緊張,護士小姐們顧左忙右,老爸被眾星拱月一般,卻突然一句「得醫生檢查了才能縫合傷口」,我們才驚覺急診部裡原來沒有醫生。等了半個多小時,醫生姍姍來遲,以惺忪的眼神判斷老爸額頭的刀傷已經止血結痂,「吃點抗生素就好」,安排我們拿藥回家,輕描淡寫地終結日常生活中突如其來的紅色警戒,以致後來我們不得不取笑那兩個攫匪愚鈍,不懂得鎖定值錢的目標:想那被盜的,是Ericsson公司未被Sony收購時生產的老舊電話,記憶體存不了十則簡訊,拆作零件也賣不到好價錢,只好下次打劫時當作榴彈襲擊下一個目標。玩笑過後,老爸休息了一天,復工作如初,眉眼上的白紗布天天更新,耀眼得很。
此後對摩哆車的聲響十分敏感,像一個真正的新山人,每每機警地往回看,老媽時常囑咐車子開到家門口,下車前要記得往車鏡裡探,注意那些可疑人士,我倒一直沒有遵循。倒是老媽自己每天這般絮叨,卻還是被歹人抓住時機,鑽進車裡輕鬆拿走了錢包,如黃鼠狼叼小雞,不費吹灰之力。接下來一整天到處辦證,麻煩得要命。許多人家為此安裝了自動閘門,省去人工開門的活兒,也省去遭遇毒手的機會。老家是新山治安黑區,三四十年的單層舊排屋,巷陌橫斜,從來不設警衛亭,即便是體認到事態急切,卻依然不願被陌生的警衛員以鐵閘區隔鄰里的敞曠,至於自動閘門也一直懶惰去換。鄰居間為此曾設立了一個志願巡邏隊,收了幾次維持費後也不了了之,街道依舊。
說是如此,開車送人回家的時刻,還是養成習慣一定要親眼見到人家走入兩層家門後方肯離開,確保自己以車子擋在人家大門前,歹徒不至於有機可趁。想,人家定要回身鎖門的,一轉身自然要打個照面,點點頭微笑揮手送別,隔著幾重門卻十分親暱。這些瑣碎的細節一直奉行至今,像是新山生活的憑據,嘮叨而又溫柔。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所在。
载2012年3月1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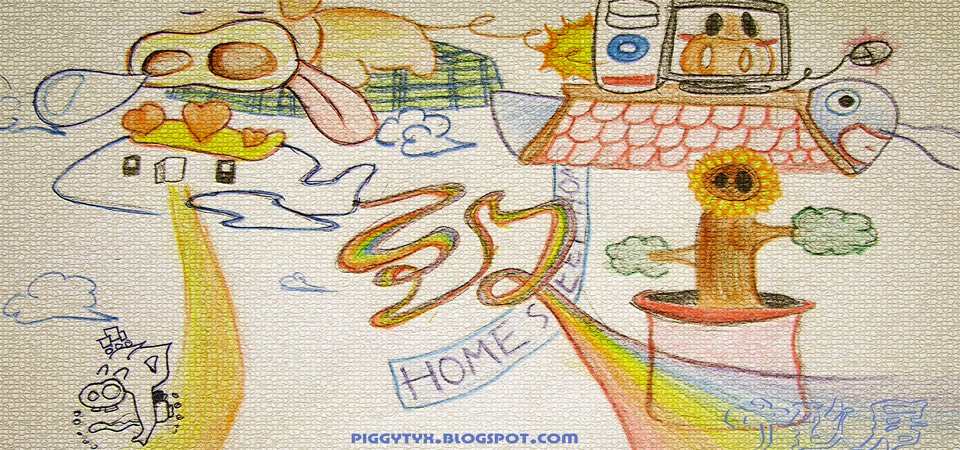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