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汁是黄黄色的浓稠液体,当它在一个早晨洗浴声琳琅响的浴室里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刻,有一种很凄凉的苦涩,我大抵知道我确实是病了。
11月中旬从初冬的莫斯科回到赤道线,迎接我的并不是和煦的阳光,柔佛海峡两岸都沉浸在阴雨的灰色之中,长命雨啊,下个不停,我下飞机的那刻,突然觉得赤道的温度可能比莫斯科摄氏一度的感觉还要冷,有一种透进身体内部的寒,或也是因为脱下卫生衣羽绒服的关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热带的雨季逮个正着,而半岛东岸的地区也全被雨水浇成片片汪洋。
两个多星期里瘦了五公斤,公司内设那位家庭医生还有姐姐介绍的那位名中医师都纳闷是不是我家里的磅秤坏了,搞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直到那个每日递减的数字以小数点一位的精确程度提醒我,我才发现,那些医生原只不过是嘴上的猜测,对我没有诚挚的关怀,我的证词没有被法官在下判时做任何考虑。只因为没有发烧,便排除急症的可能,医生胡乱给我胃药,医师也按剂量配了药粉搅成药水,结果下肚的大多被吐出来,这种反胃的感觉充斥着最近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都感觉有东西卡在咽喉,咳嗽,然后引起想吐的冲动,面对什么食物都提不起胃口。
这种感觉已经维持两个多星期,真是什么也吃不下,有时甚至意念里出现了食物便感觉恶心。这几天一早醒来,当牙膏接触到牙齿的瞬间,原本已经缓和的胸口马上又胀起,一片郁结,刷牙漱口洗脸后,依旧完全无法进食,只好正装出发,到约好的地点,开始采访工作。那天没想到聊得兴起,快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满嘴酸楚地拜别他,赶紧下楼找寻公厕,竟还有余裕地把门锁上,脱下背包挂在门后的银钩,才翻身对着马桶倾吐,只是腹中空虚什么也吐不出来,一连串的酸水,双眼泪腺也敏感起来,任由肠胃在腹腔里向上收缩,像一个倔犟的气泵,用力地发泄不满,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出现好莱坞电影中男演员被打到内伤呕血涨红着脸青筋迸发双眼发红,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当医生的姐姐对我也只是束手无策,而专科医生的排期竟还得等到两个星期后,不知道那时是已经康复了,或撒手人寰,对于生活安逸的我们,大抵只有交通意外或突如其来的无名病毒能让我们一夕升天。为此患病初期还去验血,确证实并非时下流行的蚊症,医生振奋地恭喜我让我不必担心,但报社一位编辑却说,是蚊症还好,最怕是无名的病毒,无从拯治。还真大吉利是,仿佛被他说中一般,只是为何我们总认为生病是受到某种外在的侵略,而不是我们自身内在出现了问题?我只是好奇,好想像小时候一个英语节目里的主持人们,通过很粗糙的电脑效果,把自己变小,乘着飞船进入生病的小孩的身体,看那些痰的形成,看白血球、巨噬细胞的工作程序,描绘一场无远弗届的人体星球大战,印证了合天人合一,人体与宇宙的神秘关联,也印证了我小时候的天真无邪。
办公室此起彼落的咳嗽声,仿佛每天都在回应着我,让整个办公室充满恶质的战鼓声,催逼着士兵前进,日复一日,却总听不见鸣金收兵的号令,没有谁发出集结号,工作照做,生活照跑。同事们也渐渐厌烦那些久病不愈的家伙,让办公室的天气阴霾忧郁,传染了大家一起沉沦。于是我渐渐不敢和他们共餐,深怕那些怎么吃也吃不完的餐食会让彼此更加尴尬,每个人的话题都只好转为清冷的问候,我只能不断复述我的情况,加上咳嗽以博取同事们的同情。当他们报以怜悯的眼神,一场午餐终于结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击打键盘,直到下班,不再交流。
像以前阿嬤还在的时候,她总是会说嘴巴苦苦,吃不下饭,终于明白阿嬤所谓的苦苦,是每天早上起床时,大量唾液分泌到口腔里,却不知什么因由唾液很稀,稀得像某种劣质牌子制造出来的过分蒸馏漂白的矿泉水那样带点苦涩,顿时让人失去所有食欲。这几天,吃稀粥比吃药更能让我成为一个完全的病人,淡而无味的粥水却竟是最能下肚的东西,哪怕蒸蛋、炒青菜、肉片弄得再怎么入味,就只有粥是最后的良药,好像是在提醒我,不要总是贪图浓郁的滋味,那些华美的东西在你最不舒服、最低落的时刻都无法陪你度过难关,但白粥的所有隐喻都指向褪去色彩的姿态,并且脆弱得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令我揣揣不安,白色如神经病院,某种白色的神经质,某种白色的恐怖色调,还有悼亡时候的白色。或许因为这些秘密的象喻系统,吃多了白粥,感觉整个人都变淡了,仿佛无时无刻会被光穿透身体,但庆幸的是,这连续十多天里,都没有机会见到任何成束锋利的阳光。
就在出发莫斯科的一周前,我飞到吉隆坡参加朋友的婚礼,婚礼上我犯了胃病,食不下咽,无论吃什么都只有进一步牵动肠胃的神经,坐在两旁的女性好友,一个握紧我的左手在虎口上按摩,另一个抱起我的右手,用力搓揉内关穴,尽管痉挛的胃毫无起色,但那个画面却总有金庸笔下令狐冲到处受人医治时的情怀,一时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其实又有点尴尬,最后新人来敬酒,只双唇略沾了点红酒,一切又变本加厉起来,但仍必须努力保持笑容,拍了张婚宴上最能彰显幸福的大合照,完美地结束这场喜宴。胃抽筋不似脚抽筋,掰开脚板就能舒缓,只能花几个小时让它耍脾气累了自己平复,真像一个小皮蛋,闹起别扭可真够呛的。我不知道婚宴上那次闹闹脾气与最近一连串反胃有什么关联,但感觉上这家伙已经到了叛逆期,越来越不受控制。
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降到高中时期的体重,仿佛一下子把这几年生活外加给我的东西一下子甩掉,肚腩消了,大腿上皮与肉贴得更紧了,窄管牛仔裤失去了效果,是瘦了,但却不是高中年代那时候从早到晚打球踢球练合唱训练出来的精炼。现在的我,奔跑已经成为奢侈品,就算要错过地铁或巴士都不愿意再跑了,绝不愿意弄乱头发和衣衫,想忘掉那股拼命追袭而变得狼狈的样子。
照着这个趋势一直瘦下去的话,可能不久后真的会变成风筝被风吹起来,但最近阴雨的天气应该不会让我飞得太自在吧,夹杂着闪电,随时要被打落,烧成黑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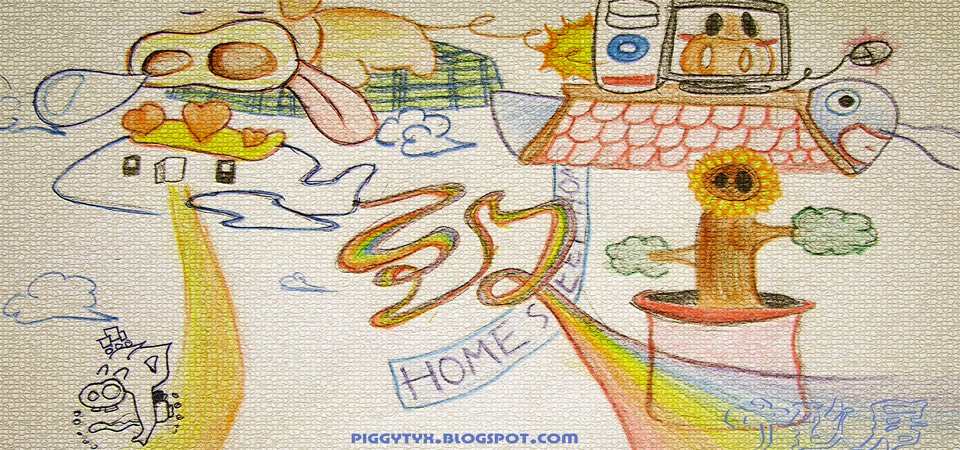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