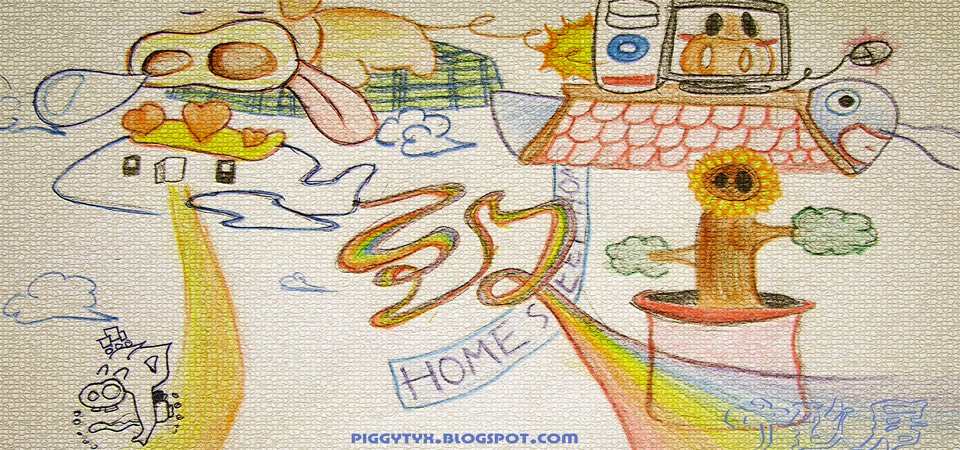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
| 英培安第一次跟草根书室买书 |
陈宇昕/文
走进新的草根书室,迎面是放着绘本书和新书推荐的“小岛”,正门右边有一个小展示柜置放精美的手工笔记本,新东主之一林永心说,这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男艺术家巧手编绣的作品,购买者还可以要求他绣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都是桥北中心的旧草根书室所没有的。
上周六下午才刚尝试营业,新草根书室位于文化气息浓厚的武吉巴梳路,和许多历史悠久的会馆、湘灵音乐社、复古的大华酒店等毗邻,店面更加宽敞,洋溢崭新的气味:新漆的味道,木制橱柜木屑的气味,还有书本特有的书卷香气。
草根书室易主,在小小的新加坡华文阅读圈子里算是件文化大事,多少年来人们习惯把草根与英培安视为文化共同体,这家本地极少数的文人书店,甚至被视为新加坡的文化地标,更有许多国外的爱书人在旅游时特地走入桥北中心那栋已经没有什么门市店面的大楼,通过那台经常出问题的电扶梯走上三楼的草根书室。
草根书室易主已经三个多月了,林仁余、林永心和林韦地三人,从英培安手中接过书店,在桥北中心店面租约到期之后,物色了新地点。上个月18日,旧草根书室举办告别仪式,英培安到场和老顾客叙旧,到访的人把书店挤满了,这是书店营业20年少有的情景,发生在告别那天,让人多少有点五味杂陈。
英培安这些年患癌,碰上官司,这些事情在生理和心理上给他很多压力,加上书店经营近20年从未盈利,苦撑许久,他把写小说的收入、文学奖的奖金都用来补贴书店的亏损,还得花时间精力营运,压缩了自己的创作时间。英培安每次受访时都说,一想起书店就泄气,自己好像花费精力在经营人们不需要的东西,但每次想要结束营业,却又觉得可惜,想要继续为支持他的老顾客撑下去。不知不觉20年就过去了。
新东主林仁余、林永心都是草根书室的老顾客。70年代他们就常光顾英培安在黄金大厦经营的前卫书局。
林仁余说,几年前英培安和他提起要结束草根书室的想法,他还劝英培安果断关店,文化责任不应该只落在一个人身上,但随着时间推进,桥北中心店面租约的大限将近,他又感觉不妥,书店不应该就这样结束,每个城市应该有一家优质书店,于是他和好朋友林永心讨论起来,就像他们平常爱谈的开咖啡店、开书店的理想,谈着谈着,竟认真起来想要付诸实践。
与年过五十的林仁余、林永心不同,今年刚30岁的林韦地与草根书室的缘分比较浅。槟城出生的他,在英国曼彻斯特读医科,两年前毕业来到新加坡工作。他也是作家,在朋友介绍下拿着新出版的散文集《于是》到草根书室寄卖,和英培安一见如故,聊了许多,他也不希望书店关闭,想要出一分力,便在英培安的牵引下和林仁余、林永心见面,才有了今天的三“林”组合。
如今林仁余和林永心两人全职负责书店业务,林韦地则医院书店两边跑。
林韦地说,他17岁那年获得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新秀组奖项时到吉隆坡参加花踪研讨会,英培安正好是主讲嘉宾。当时他通过主办当局订酒店,结果拿到错的钥匙,他开门时发现门已反锁,结果走出来的人正是英培安,没想到十多年后他竟然又碰到了英培安,还接手了草根书室。
为什么对草根书室有如此特殊的情感,林韦地说,草根书室让他学到很多,看到架上那些文史哲书籍,他觉得自己渺小而变得谦卑。其实在这之前,他对独立书店的了解并不多。
采访那天,书店刚试营运一天,还有许多琐碎事物有待处理,林仁余精心设计的烘焙室因供电问题还没能运作,位于书店最深处的咖啡厅还没成型,书本之外的文具等小商品也还没上架,一切或许还要等一两个月后才能完成。
草根书室近20年来主要售书,偶尔会举办一些文化沙龙,新的草根书室,在空间的运用上展现了更多可能,12月中旬,绘本作家阿果新书发布的活动将在草根书室进行,届时活动式的书墙能成为展览壁,挂上阿果的画作。除了文学活动,三人策划未来在店内举办影音放映、手作工作坊、小型展览等文创活动,让人们与书店空间有更多互动。
林仁余说,这些做法都不新,近年国外媒体都在评选世界最美的书店,书店成为文化风景的重要坐标,说明面对经营危机的实体书店正在以新的方式回应局势。纯书店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可能了,尤其在新加坡,店租与工资只会越来越高,书店必须拥有其他的利润来源以平衡收支。附设咖啡厅是热爱烘焙的他最自然的选项,他也希望借此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
林韦地则认为实体书店的空间概念是网络书店不能提供的,他们希望能创造一个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自己所长。他始终相信“实体”的力量,觉得现在人们太高估网络的影响力了。
拜访新草根书室之前,我出了个题,希望他们各给我推荐一本书。林仁余推荐的是森下典子《茶道带来的十五种幸福》,林韦地推荐的是马华作品杨邦尼《古来河那边》与陈政欣《文学的武吉》,林永心则忙着招呼其他客人,把受访的任务交给了她的两个伙伴。
林仁余近年醉心于烘焙与烹饪,他说自己有个梦想,希望未来书店能在午夜12点的时候举办“深夜食堂”,亲手下厨煮几道菜,一直吃到凌晨4点。他对烹饪烘焙的兴趣也改变了他的阅读取向,年轻时喜欢文学创作,虽然现在也还在阅读文学作品,但像《茶道带来的十五种幸福》这类作品现在更深得他心。书中谈到手艺的传承,谈人们在以手劳作的过程中,将一门手艺化为感受生命的媒介,让他颇有感触。
林韦地介绍的则是来自他家乡的作品。《古来河那边》与《文学的武吉》分别描写作家生长的柔佛古来与槟城大山脚。他说,在全球化时代里,人们总追求流行事物,这引起不少人反思自己与生长的土地的关系。地方书写因此有着重大的正面意义,这也正好与独立书店的特质相关。
一家书店最重要的就是选书,书本内容决定了书店气质,草根书室20年来总显得孤绝,除了书店位置不佳的关系,英培安强调文史哲的选书理念,有时也让一些读者却步,担心读不懂。
草根书室有其独特的历史,其实当初三人有两个选项,一是接手草根,另一个是开设一家全新的书店,或许创新会比传承来得容易。
那为什么决定接手?林仁余说:“这个城市少了一点延续。”他继续说,书店还是会保持文史哲书籍的格局,但三位经营者各有其阅读兴趣,因此书店内容会有所扩张。林仁余喜欢绘本书、饮食相关的书籍还有旅游书,林韦地喜欢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林永心则喜欢手作文创作品,店内一些古董家私也是她的私人藏品。
现在的草根书室已明显有不一样的气质。
英培安曾说过,将书店交给三人他很放心。林仁余也说,英培安曾嘱咐他们不要有旧草根的包袱,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理念。回到根本,其实书店的特质是顾客塑造的,而他们要做的是,从每一种类中挑选最优质的书本。草根书室单凭三人之力绝对没办法继续下去,需要更多朋友和顾客给他们意见与帮助。
最现实的问题,是人们需不需要这么一间书店?
林仁余说,即便书店是文化产业,但处在一个商业社会,没有消费行为,实体书店不可能成立。他们现在投入的资金大概足够让书店维持两年半,到时候还没能取得收支平衡,书店没办法继续。他认为决定权就在消费者手里,人们不能一面叹息实体书店消逝,另一方面却无动于衷。
谈到传承,林韦地坦言这是个很尖锐的课题。面对过去,面对忠实读者的期待,要传承,压力很大。
的确,草根书室易主换店,在华文阅读圈子里引起不少讨论,许多人在新址还未开业之前就悄悄拜访了书店,期待满满。忠实顾客荆云(张淑华)就期望草根在新地点扎根后,能延续强韧生命力,带进更多好书,散发魅力,让所有人能在岛国享受阅读乐趣。
期待的人当然也包括前东主英培安。
采访那天,英培安和太太吴明珠到书店逛逛,看见新书店内中央放着从旧书店搬来的一张木制办公桌,上面摆满了英培安的作品,成为一个小专柜,他高兴地应邀拍照留念。林永心领着他参观,介绍他新书,包括不少中国出版品。以前英培安专门经营港台出版物,新的草根现在则添购了一些中国出版书籍。
英培安告诉我,新书店给了他一点“诚品书店”的感觉。那天临走前他买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米兰·昆德拉最新作品《庆祝无意义》,付款的时候还兴奋地说,这是英培安在草根书室买的第一本书。
·草根书室,武吉巴梳路25号/营业时间:每天上午11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
文载2014年11月18日《联合早报·现在》封面